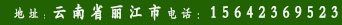|
年5月底,随着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临近,神十飞行乘组也转入最后隔离阶段。在隔离前夕,《航天员》杂志与央视、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共同采访了这3位即将出征太空的航天员。他们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既流露出将遨游太空的激动与兴奋,也展现出肩负使命的稳重与自信,同时也与我们分享了飞天前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和感想。 年6月26日上午8时07分,神十返回舱顺利着陆,随着神十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安全出舱,神舟十号任务也圆满完成。任务后,这3名航天员就进入了21天的医学隔离恢复期。《航天员》杂志又于第一时间对这3位英雄进行了任务后的首次独家专访,进一步分享了他们15天太空生活的经历和感悟。 通过与神十航天员最近距离的交流,我们被3位英雄的航天精神和侠骨柔肠感动、感染,相信呈现在广大读者朋友面前的也一定是一场独一无二的精神盛宴! 中华骄子王亚平 首位太空教师 在挑战中成长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80后’是敢于迎接挑战的一代。”这是即将在太空闪亮登场的80后女航天员王亚平,在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时铿锵有力的回答。这位在聂海胜、张晓光口中的“女孩儿”“小姑娘”有着一种不惧艰难挑战的倔强,她的智慧和美丽感染着每个见过她的人,她将成为中国首位太空老师。 终于可以自己飞了 ■问:您当初为何选择当飞行员? ■王亚平(以下简称王):纯属巧合。我们高考那年正好赶上我国招收第七批女飞行员,而且那时候招收名额很少。因为感觉希望不大,我本来没想去的,不过当时我们理科班有二十多个女同学,我是唯一一个不带眼镜的,所以同学们极力鼓励我试试。我在她们的“怂恿”下去了。后来,没想到一路过关斩将,竟然选上了。 ■问: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作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飞上蓝天时的感觉吗? ■王:记得我第一次单飞时,起飞的时候我就扭头看了后面,教员不在,心里特别高兴,我就在座舱里大喊了一声。 ■问:是因为终于自己一个人可以飞了吗? ■王:对,是啊,终于可以自己飞了! ■问:您喜欢挑战么? ■王:喜欢,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在不停的挑战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 ■问:能给我们举个是您感觉您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去挑战成功了的例子吗? ■王:上军校跳伞的时候,我们当时要跳两次。第一跳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奇,一个一个毫不犹豫就都跳下去了,我是第四个跳下去的,跳的过程没什么感觉,稀里糊涂就下去了。但第二次跳时大家都后怕了,座舱里鸦雀无声,一直到准备跳的时候,都没一个人说话,但最后自己还是挑战成功了。 ■问:跳伞完后的那天晚上后悔过当飞行员吗? ■王:没有。我记得那天跳完后,在回去的车上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唱了一首歌——《真心英雄》,因为所有人觉得那对自己是一个挑战。在那9年驾驶运输机驰骋蓝天的过程中,我也是不断接受挑战,所以才能完成奥运会开幕式消云减雨、汶川抗震救灾、山东抗旱等任务,才能安全飞行多小时。 十年一轮回的飞天梦 ■问:从事航天员职业与您的兴趣和梦想有关吗? ■王:03年杨利伟首飞的时候,我23岁,也就是10年前,还记得发射当天,我们很多同学一起在电视机前看。发射那一刻,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是十分激动的。当时,我内心瞬间有个想法——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男飞行员和女飞行员,现在又有了自己的男航天员,那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女航天员呢?真的没想到10年后的今天,我自己能飞上太空! ■问:当航天员的生活跟您之前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当航天员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不仅要学习海量的知识,进行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而且还要接受近乎苛刻的零失误、零差错的考核。 ■问:您刚才用了“苛刻”这个词,怎么样才能做到零差错? ■王: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能出现任何的走神、分神。而且我觉得要保证零失误、零差错,乘组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协同也是极其重要的。 ■问:上次看到刘洋飞上去,有什么样的感觉? ■王:去年在他们发射当天,大队长临时让我们给他们每个人说一句祝福的话。我是最后一个说的。我说,首先我想跟乘组的三个人说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平安回来。然后我想跟刘洋单独说一句,你是我们女同志的骄傲,我希望你能带着我们俩的梦想一起去飞,我会在地面永远支持你。 ■问:能说说你们团队是怎样的氛围吗? ■王:像聂师兄(聂海胜),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成熟稳重,非常值得信任的老大哥。有什么事情如果有他在的话,我都觉得很安心。我经常把他比作我们乘组里的“定海神针”。然后,张师兄(张晓光)是一个很热情,很开朗的人,也是我们团队里的开心果,每次只要有他在的话,都会很愉快。 精心备战太空授课 ■问:太空授课是亮点。您一下子从航天员转变为老师,此前试讲听说您讲得很好,这么快成功转变角色有什么窍门? ■王:没什么窍门。我一点当老师的基础都没有。其实,刚接到这个任务时,也有点压力,就是怕进入不了角色,找不到当老师的感觉,让同学们接受不了。但自己还是坚持慢慢练,我会经常把练习时的录像拿过来看。可能自己讲时很难发现问题,但是自己看自己讲的录像就能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这个语调太平淡了,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或那个地方动作不太合适,应该换成什么动作等。基本上都是自己看,自己研究,慢慢的就好一些了。而且,那时还请了北京中学和人大附中的老师专门来给我们讲课,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我会仔细观察他们是怎样讲的,然后吸取他们的长处,不断地练习。所以说,没什么窍门,就是一遍一遍的讲,一遍一遍的研究,然后就发现一次比一次好一些。 ■问:太空授课内容您都背下来了? ■王: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要背,其他口语化的东西不背,不然40分钟的内容根本就说不完。讲课时自然就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每次试讲内容都不太一样,但原则性的东西基本上不会变。 ■问:这次飞天对您来说,现在能预想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包括身体上或心理上的? ■王: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对于授课内容这方面的天地差异。因为在地面模拟得再真、再好,但在失重环境下可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甚至有一些实验做不了。所以我们上去后就要提前训练、试验,如果有些实验做不了就启用备份项目。或者某实验中的某个现象显现不出来,我们就要调整脚本,看怎么讲更好。毕竟是第一次,到底怎样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挑战还是很大的。 ■问:您的任务除了太空授课,还有什么? ■王:呵呵,我的任务挺多的。第一,飞行器状态的监视和设备操控;第二,进行一些在轨的试验和空间实验;第三,具备手控交会对接的能力;第四,主要负责太空授课,还有乘组的生活照料。 习惯了,就好 ■问:这次飞行有没有带一些化妆品之类的上去? ■王:还真有,这次任务我认为考虑得很周全。专门为我们女性准备了一个包,有很多女性专用的物品,包括护肤品。只是考虑到失重环境,我们女同志平时用的爽肤水就不能带,它是液体,带上去用的时候会飘出来。 ■问:听说你们带的小镜子都是铁片的,照起来有些模糊吧? ■王:是的,而且是我们三人共用一个镜子。之所以不用玻璃的是怕发射的时候把它震碎了,铁片的虽照不清楚也能将就着用。 ■问:太空摄影在航天员领域是比较流行的,在太空摄影有什么难度?能否说一说这在地面上怎么训练的? ■王:我觉得太空摄影的难度应该是太空失重不好固定相机。我们在地面对摄影确实经过专门的训练。其实,太空摄影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东西你看到,但可能描述不出来,只有拍下来了才是一个永久的纪念,永久的再现,可以让更多的人看。 ■问:上一次逛街是什么时候? ■王:不太记得了,应该是好几年前,去年一年至少一次都没有。我们加入这个队伍后3年的时间也就出去过两三次。 ■问:这会让你觉得缺什么吗? ■王:不缺。任何时候都是一种习惯! ■问:这么忙,都顾不上家,您爱人没意见吗? ■王:没有。他是无私的支持,全力的支持。所以任务后,希望能陪他吃顿饭,逛逛街,看场电影。 ■问:任务完成回来,想吃点啥? ■王:呵呵,估计到时候啥都好吃。 当多万学生将目光投向太空,聆听她为他们演示和解惑太空神奇现象时,航天员王亚平俨然已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师;当地面上此起彼伏的掌声在为她精彩的讲课喝彩时,“王老师”的完美形象已定格在每一个渴望知识,热爱科学的学生心中。在神十任务完满完成之际,《航天员》再次走近王亚平——中国首位太空老师,分享她此次太空之旅的诸多收获。 “王老师”,我听着高兴 ■《航天员》(以下简称《航》):太空授课即将开始前,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王亚平(以下简称王):太空授课之前,我感觉大家情绪都挺稳定的。但前期准备时间花了很多,一切准备好了,没事了,我们就说打太极吧,我感觉那时候打太极拳意义不太一样,并不是为了稳定,而是反映我们当时的状态很好。于是就在当天课前,我们3人一起打了一套太极拳。 ■《航》:天地互动时,学生也特别积极。 ■王:孩子们都很可爱。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跟真正的学生试讲过,所以当时听到同学们的掌声,情绪一下子就比较高昂,而且感觉他们问的问题都非常好,很有代表性。 ■《航》:在太空还能做其他方面的物理实验吗?还有哪些备份实验? ■王:可以呀。我们有两个备份实验,一个是验证液体表面张力的,是拉液桥,还有一个是小球碰撞实验。 ■《航》:收到美国太空教师芭芭拉·摩根的信件,您是否感到意外? ■王:确实挺意外的,我没想到咱们这个太空授课能引起这么广泛的白斑医院有哪些白淀疯
|
中华骄子在挑战中成长神十航天员王
发布时间:2017-6-15 17:27:50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 下一篇文章: 跳绳能瘦腿吗跳绳减肥的有效方法